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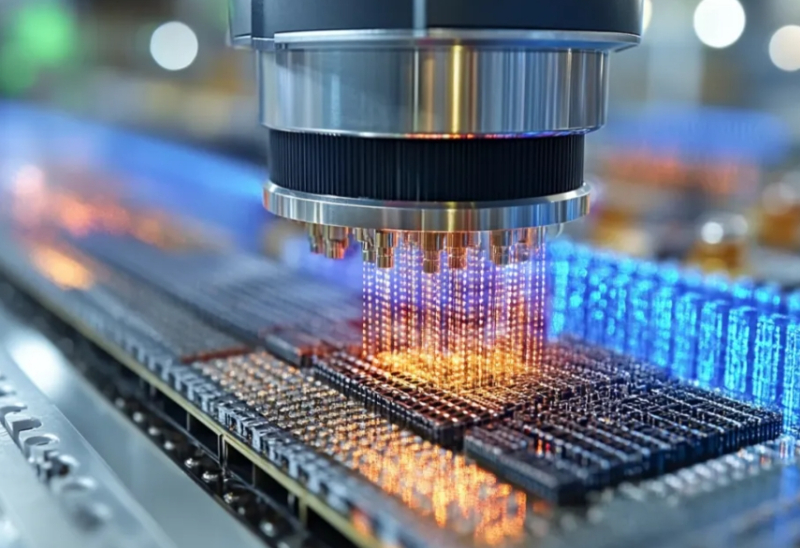
作者:五柳先生读书笔记
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半导体技术人员,当时日本的半导体存储器DRAM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以世界最高质量著称,被称为“产业中枢”,然而在2000年,日本却不得不黯然退出半导体市场。
仅存的一家是NEC和日立DRAM合资的企业尔必达,虽然其技术实力优于三星,但它还是在2012年2月破产,被美国镁光科技并购。日本半导体产业退出DRAM后,开始进军数码家电及汽车用半导体SOC市场,并上马了大量国家级项目。
但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陷入赤字,尤其是日立、三菱和NEC合资成立的瑞萨电子,虽然在汽车用半导体领域,以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40%这一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和世界最高品质闻名业界,但最终却陷入倒闭危机,被以官民基金“产业革新机构”为中心的官民联合资金收购。
过去日本的核心产业——电视产业,在数字电视领域以世界最高画质闻名,然而在2013年3月,索尼、夏普、松下的赤字合计达到100.6万亿日元,三巨头纷纷更迭社长,采取大规模裁员措施。
日本的半导体、电器产业以及英特尔等都有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都曾位居第一,都曾创造出世界的最高品质,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尽管如此,它们最终都失去了市场,从产品制造中退出,经历破产、覆灭,最终陨落。它们所涉及的各行业和企业都没有与时俱进,没能及时更新换代,陷入了“创新窘境”。
所谓“创新窘境”,即世界巨头企业过于忠实地倾听现有顾客的要求,因而导致被那些尽管产品性能和质量不高,却具有“便宜、小巧、方便”等特征的颠覆性技术的企业所淘汰。
针对大型机厂商曾提出的“给我们生产永远不坏的DRAM”的要求,日本的DRAM厂商不计成本,真的生产出了质保高达25年的高品质DRAM。无独有偶,丰田要求瑞萨电子生产零缺陷的汽车半导体(微型电脑),于是,瑞萨电子一次次反复测试,即使公司陷入赤字、入不敷出了,也没有放弃生产高品质的微型电脑。
虽说都是DRAM,但是日立和NEC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毫无兼容性可言。因此,尔必达成立仅两年后,其市场占有率就降到了原来的1/4,公司濒临破产倒闭。
对最多5年就会被更换掉的PC,却要求用于其中的DRAM具备25年质保的高品质;对于那些安装在汽车上,却很可能一次都不会使用的气囊用半导体(微型电脑),日本厂商一心追求着零缺陷;虽然电视的画质早已超越人眼的辨别范围,但日本厂商依然在追求画质的提高。
日本大部分电子企业不能够与时俱进、更新换代,从而陷入创新窘境最终导致落败。而且,它们在技术层面则完全输给了成功转型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企业。
日本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在2007年达到12.2万亿日元的顶峰后,2010年减少到10.5万亿日元,2011年日本国内的设备投资仅为1990年的70%。以电器产业为例,松下、索尼、夏普三家公司的设备投资金额合计为100.0136万亿日元,还不及韩国三星一家公司的100.5788万亿日元。
我在日立中央研究所、DRAM工厂、设备研发中心时,从未怀疑过日本的技术和技术实力。日立所有员工都深信日本技术无疑是世界最强的,我也认为自己的技术是世界第一的。当时我们只将竞争对手锁定于国内的东芝和NEC,根本没有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放在眼里。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韩国三星电子公司迅速成长,与此相反,日本DRAM的市场占有率却不断下滑。结果,仅凭1家公司难以独立运营,1999年12月,日立和NEC成立了DRAM的合资公司尔必达。而东芝、富士通、三菱电器等不得不退出DRAM舞台。
我于2000年2月自愿从日立借调至尔必达。后来耳闻,最初借调至此的800人中,毛遂自荐的只有我一人。或许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手连日立和NEC都维持不了的DRAM这个烂摊子。那时,我才开始怀疑日本的技术和技术实力。
让我震惊的是,即使是生产同样的DRAM,日立和NEC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工艺流程、装配、相关的技术人员种类和人数等都大相径庭。最大的分歧在于两个公司对技术和技术实力的看法及哲学思考完全不同。
在尔必达内部,日立与NEC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技术霸权争夺战。因为日立和NEC都认为自己的技术实力是世界第一。我在尔必达内部斗争中成了NEC的手下败将,被贬为科长,失去了部下也失去了工作,最终被尔必达扫地出门。
后来,从2001年4月开始,我进入半导体前沿技术公司研发协会(通称Selete)。Selete是由13家半导体生产商共同成立的半导体共同研究机构。在日本产业界,伴随着世界市场占有率的降低,就会出现由国家主导成立类似这样的联盟。
此时除了尔必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各大公司均退出DRAM市场,转向了SOC。所谓SOC是“system on chip”的简称,是将处理器和储存器等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实现一系列功能(系统)的半导体,也称为“系统LSI”。尽管成立了以“Asuka计划”为代表的诸多联盟和国家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集结了日本半导体厂商的技术人员,但是日本的SOC依然陷入了不可挽回的状态。最终,瑞萨电子面临破产,富士通和松下合并了设计部门,东芝SOC业务的规模大幅缩小。
2000年IT泡沫破灭,半导体产业陷入极度萧条的处境。这导致日本半导体厂商进行了大规模裁员。日立裁员2万人,东芝1.8万人,富士通1.64万人,NEC 400人……我所在的日立,对半导体相关部门提出了“希望40岁以上、课长职位以上的人员全部自行退休”的提前退职劝告。我当时正好40岁,并且担任主任研究员(课长级),接到了3次提前退休劝告。估计由于我那时正借调到Selete,所以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2002年10月,我决定离开工作了15年的日立。然而虽然接受了日立的提前退休劝告,我却无法享受到《提前退休制度》的待遇。我被定为因个人原因退职,最终只领到了100万日元的退休金。
制造半导体,需要经过由高度集成技术构筑的500多道工序,所谓买了装置排成一排按下按钮就可制造,简直是无稽之谈。
所谓半导体,正如其字面意思所示,是指电阻介于金属等“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质。有很多物质都是半导体,地球上最多的就是硅(Si)。往硅中注入杂质后,它便成为导体,而将之氧化后,它又会成为绝缘体。利用硅的此类性质,可以在硅片上安装电开关或者放大元件。这就是晶体管。
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半导体”并不是指半导体物质,多数情况都是指“半导体集成电路”。因此,“半导体产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
所谓半导体(集成电路),就是在半导体材料硅基板上集成无数个晶体管、电容、电阻等,使其实现一定功能的电子电路。美国英特尔于1971年发售了用于计算机的半导体处理器“4004”。该处理器中大约集成了2300个10μm的晶体管。从芯片价格逆推计算的话,平均每个晶体管成本约1美元。2012年,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处理器酷睿i7上晶体管的集成度达到了14亿个。正因为想在一个芯片上植入更多功能,所以才要将晶体管高度集成,与此同时,晶体管自身也在不断精密化。
自1971年至2012年的41年间,一方面,晶体管集成度提高了60万倍,但另一方面,其大小精密到了原来的1/1000。虽说成本的降低不是完全得益于精密加工,但是据粗略估算,精密加工的贡献率高达80%。我们将光刻技术与蚀刻技术共同称为精密加工技术。
此外,还有CMP(化学机械抛光)技术、离子注入技术、热处理技术,等等。简而言之,半导体是在25~30次地反复进行“成膜→光刻→蚀刻→清洁→检测”这一循环后,通过在硅片上形成三维结构而制造出来的。
结合组件技术,将半导体植入硅片,构建这一工艺流程的技术就是集成技术。譬如在生产DRAM时,要制定500道以上的工艺流程。批量生产移交的方法有精确复制和基本复制两种。
如果研发中心和批量生产工厂的设备属于同一机种,一般会直接复制工艺条件,这就是精确复制。但是如果两者设备不同,为得到相同的工艺结果,就必须调整工艺条件,这就是基本复制。毋庸置疑,精确复制要比基本复制更容易进行批量生产。
但其实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精确复制基本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即使研发中心和批量生产工厂的设备相同,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也未必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坦率地说,一般情况下难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是因为即使是同样的设备,两台机器之间也会存在微小的性能差异。这种差异称作机差。机差可以说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厂家在生产同一型号的设备时,因不可控因素的存在而可能产生的设备差异。
随着半导体精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机差问题也日益显著。也就是说,随着精密化程度的提升,需要实施高精度的加工,此前生产过程中不会成为问题的微小的机差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一般来说,刚从开发中心将工艺流程转移到批量生产工厂的阶段,批量生产工厂的成品率几乎是0%。而将成品率尽快提高到接近100%,并且长期维持接近100%的成品率的技术,才是真正的批量生产技术。在需要进行大规模调整时,该工艺流程就会被退回开发中心。更不幸时,则可能需要重新设计。这样,从开发中心最初制定的工艺流程到形成能使批量生产工厂获得高成品率的工艺流程,通常需要5~10次反复。
当时DRAM多用于大型电脑和电话交换机等设备。当时大型电脑制造商以及日本电报电话公共公司(现为NTT)要求“制造不会出故障的DRAM”。其技术标准是,大型电脑要有25年质量保证,电话总机要有23年质量保证。可以说这种无理的要求简直让人无计可施。但令人生畏的是,日本半导体制造商居然真的制造出了这种对可靠性要求极严格的高品质DRAM。
因此,日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脑业界迎来更新换代。PC取代当时的大型电脑占据了主要市场。电脑界的更新换代也导致了DRAM需求的变化。DRAM的主要消费商也从大型电脑转向了PC。伴随着这种更新换代,日本DRAM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而韩国则取而代之,特别是三星电子获得了飞跃发展,并最终在1992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霸主。此外,美国凭借镁光科技有限公司这家DRAM制造商,也于2000年在市场份额上赶超了日本。PC用的DRAM所要求的就是低成本和数量(规模),而不需要25年质保这样的高品质。
韩国三星电子和美国镁光科技通过大量生产(不需要25年质保的)廉价的DRAM,在市场占有率上超过了日本。尔必达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资金,投资都来自母公司日立和NEC。
2001年批量生产工厂建成之时正是IT泡沫破灭之后,电子业界遭遇空前的萧条。日立和NEC均无余力向尔必达进行设备投资。结果,最先进的批量生产工厂徒有其表,内部并未购入制造设备,从而成为空壳工厂。正因如此,尔必达才未能生产出原来计划的DRAM。
日立的批量生产工厂中约60%的制造设备都和NEC相模原研发中心的制造设备不同,这样便不能直接移交工艺流程。为了能够用不同的设备获得相同的工艺特性,就必须对基本复制进行返工,从头再来。基本复制所需要的工序越多,批量生产工厂的负担也就越重。
此时,需要通过基本复制对60%的工序进行重新制作,但是在批量生产工厂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基本复制作业的。
在NEC相模原的研发中心制定的DRAM工艺流程,需要在日立的设备开发中心通过基本复制修改为符合日立规格的工艺流程,然后再将此工艺流程移交给日立的批量生产工厂进行生产。但是这样一来,两家公司合并的优势全无。
不要说优势了,作业反而变得更加烦琐和低效。这种烦琐的移交作业由于过于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后不得不中止。甚至部分工艺无法修改成符合日立规格的工艺,即DRAM工艺流程中大约占30%的清洗工序。半导体制造的清洗液就如同人类的血液一般。虽说成分相似,但是却不能轻易向其他人“输血”。
此外,清洗设备必须与清洗液匹配,属于特别订购产品。清洗设备从订货到交货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据说NEC曾在批量生产工厂内多次实现100%的成品率。然而遗憾的是,在日立不用说100%了,我连90%的成品率也未曾目睹过。
2002年11月就任尔必达社长的阪本幸雄面对针锋相对的日立和NEC,命令道:“这里是NEC,要按照NEC的规矩办事!”设计、研发中心、最先进的批量生产工厂都在NEC的地盘里,因此这个命令是非常有效的。
而对此举反感的日立技术人员则选择离开了尔必达。坂本社长从世界各地汇集了1700亿日元的资金,为原本徒有其表的最先进工厂购置了制造设备,使得尔必达的DRAM生产走上正轨。但是由于技术人员过于关注生产而无暇顾及技术研发,因此与社长更替前相比较,你会发现公司的“技术实力并没有提高”。
NEC采取了细化分工,因此技术人员是日立的3倍之多。但三菱则截然相反,其技术人员可以说是只身从事多种技术的全能工人,一个人既可以做研发亦可做批量生产。因此三菱技术人员的人数只有日立的1/3左右。换言之,NEC的技术人员是三菱的10倍左右。三菱职员告诉我,尔必达过度使用了世界一流的高级技术,对于PC用DRAM来说,这明显是质量过剩,并且这也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DRAM。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DRAM席卷世界之际,NEC、东芝、日立、富士通及三菱被称为5大巨头。在当时的5大巨头中,三菱一直是垫底的。三菱既不能像东芝和日立一样,通过最先进的精密加工技术与龙头企业决一胜负(缺乏自信),而且也不能像NEC一样通过规模和资金与其他企业一较高低。但是三菱必须在DRAM上获利。
因此,三菱将希望转移到了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方面,而非最先进的技术。另外,三菱还将重点放在了成本竞争上,而非资金规模竞争。这样就形成了以集成技术人员为轴心,综合统筹设计人员、组件技术人员、批量生产技术人员的独特文化。
日立的新技术研发能力很高,善于去突破、攻克某一点,但是提高成品率方面的技术能力较低。而NEC则是过度重视统一性,对技术进行细化分工。虽然它在实现高成品率方面的技术实力较高,但是由于产品的工艺流程繁杂,导致其在低成本制造方面的技术能力薄弱。
“理想蓝图”就是:日立进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三菱在研发中心负责集成技术,NEC专注于批量生产工厂的生产技术。若能实现这样的合作,尔必达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DRAM制造商。
NEC员工占大多数的人员构成方式容易形成“繁杂”的工艺流程,因而导致尔必达在低成本生产技术能力方面非常薄弱。如此一来,尔必达和合并前相比没有任何长进。在尔必达新一任社长上任后,其市场份额稳步增长。
然而,尽管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但利润率完全没有上涨,这使得尔必达在雷曼危机爆发的2008年出现巨大亏损,2009年更是获批适用《产业再生法》第1号,获得了300亿日元公共资金。
随后,在2012年2月27日,尔必达最终宣告经营破产。回望三星过去的20年,其销售额的增长达到17倍以上,营业利润的增长也超过了11倍。在三星电子公司内部,从研发到批量生产,再从批量生产到研发,由各小组不断替换进行。也就是说,在制定DRAM生产工艺流程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将批量生产的启动纳入考虑范围,制定便于提高成品率的工艺流程。
因为每个小组都明白自己的使命,即让自己研发的DRAM实现批量生产。一旦建立这样的体系,各小组成员们会常常提醒自己,要注重从工艺流程的开发到批量生产这一过程的整体优化。这样一来,提高成品率的意识和成本意识自然会扎根于组员的心中。
在日本,研究所、研发中心和批量生产工厂存在着类似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和三星不同,批量生产工厂被视为最底层,被人轻视,不受欢迎。此外,组织间壁垒高筑,缺少沟通。比起成品率,日本制造商更拘泥于高性能、高品质,而三星电子为实现成品率的飞跃想尽千方百计。
举例来说,在开发新一代DRAM时,日本(特别是日立公司)“倾向于一味地引进新技术”,而三星电子则不同,如果新技术不能提高成品率,三星就绝不会引进该项技术。因此,三星电子倾尽全力贯彻“设备不变、工艺流程不变、工序不变”的理念。
三星电子在延长现有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及熟练运用设备方面拥有非常高超的技术,且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品率从60%提高到80%相对比较容易,但要把成品率从80%提高到95%,就要付出和前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努力。
也就是说,这需要花费庞大的人力、财力、时间等资源。在三星电子看来,80%以上的成品率完全可以确保其在市场中站得住脚,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去追求更高的成品率,三星也不会去这么做。成品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从本质上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降低每个DRAM的成本,增加利润。说得极端些,即使1枚晶圆只能制造出1个DRAM芯片,只要有利可图,只要能做成买卖,根本没有必要再耗费成本增加切割出的芯片数量。即使利用世界顶尖的精密加工技术实现了100%的成品率,只要单个DRAM的成本增加,这种努力也毫无意义。
甚至可以说,在“DRAM 1美元时代”到来之际,这种努力反而是无益的。从三星电子的组织机构图上可以看出,战略市场部门有员工800人,其中市场调研专员竟有230人。三星集团吸引了韩国全国的精英们纷至沓来,经过三层选拔,最后招收2万名新职员。这些新人在入职后也不能有丝毫松懈。
同年入职的员工之间将会打响一场激烈的晋升战役。如果到40岁还没有晋升为部长,就无法继续留在三星。也就是说会被炒鱿鱼。所以他们每天都要保持昂扬的学习劲头。而在日本企业里,很多管理人员一旦成为课长、部长,就渐渐远离生产车间,从而不了解最先进的技术,最终变成办公室里的隐士。
也就是说,在日本企业里,地位爬得越高,往往越无能,这种情况很普遍。NEC创立于1899年,是由岩垂邦彦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制造部门即美国西电公司合资成立的。也就是说,NEC最开始是通过与海外企业合资而创立的,可以说它本应该是一家具有国际风范的企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NEC以生产电话交换机等通信设备为主要业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日美关系恶化,NEC被合并到住友集团旗下。战后,NEC开始涉足通信、真空管和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家电、无线通信设备领域,并开始计算机的研制。
1977年,NEC会长小林宏治提出“C&C”(计算机&通信)的口号,将“计算机与通信相结合”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从此开始,NEC朝着以信息、通信为中心的综合电器制造商方向发展。
1982年NEC推出的个人计算机系列PC-9800风靡日本计算机市场长达15年之久,在全盛时期还被誉为“国民机”。1986年NEC的半导体销售额跃居世界第一,到1992年被美国英特尔超越之前的这6年内NEC都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即使被英特尔赶超之后,直到1999年NEC也始终占据着第二名的位置。
NEC将技术传授给三星电子后所生产的DRAM在1997年以前一直稳居世界前三。NEC在个人计算机领域曾是日本第一(有可能是世界第一),在半导体领域和DRAM领域曾是世界第一,在传统手机领域也曾是日本第一,NEC不愧是一家有着辉煌历史、能够代表日本的综合电器制造商。NEC从1985年到2000年间的销售额增长一直顺风顺水,在这15年内其销售额翻了一番。但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销售额开始走下坡路。
特别是从雷曼危机前后开始急转直下,从5万亿日元大跌至3万亿日元。虽然销售额有升有降,但从1985年一直到现在,NEC的营业利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换算成营业利润率平均只有2%左右。NEC只在两个年度出现过巨额的营业亏损:1998年(2247亿日元赤字)和2001年(4612亿日元赤字)。
在雷曼危机爆发的2008年,亏损额度也只停留在62亿日元,在第二年便实现盈余。韩国三星电子于1983年接受夏普的技术转让,建立了半导体DRAM内存芯片第一工厂。第一工厂的成功让三星电子尝到了甜头,于是在第二年,凭借自身的力量成立了DRAM第二工厂。然而由于该工厂的DRAM成品率难以提升,这次建厂以失败告终。可见当时的三星还没有自力更生制造DRAM的技术水平。
随后,在建设第三工厂的时候,当时三星的社长表示要让钱发挥作用,于是花高价组织了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专家咨询团(一部分人称之为顾问团)。有传言称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90年代,周末从日本飞往首尔的航班中,坐满了日本半导体制造商的技术人员。甚至有消息称,日本企业最新的技术情报以每条10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给三星电子。
可以推测,这宗买卖也是由顾问团在暗中操纵的。也就是说,顾问团联系上有意向或感兴趣的日本半导体制造商的技术人员,进行上述交易。三星电子拥有一张无比强大的信息收集网,特别是在对日本制造商的技术收集方面,三星进行得非常彻底。他们搜罗各种最新信息和机密情报并进行分析,不论合法或非法。日本三星就是他们的据点。
2003年4月,日立和三菱的SOC部门合并后成立了瑞萨科技公司。2010年4月,NEC电子和红瑞萨合并。新公司的名称结合了两家企业的名称,定为“瑞萨电子”。因为瑞萨电子的Logo为蓝色,为了和原来的红瑞萨区分,新瑞萨被称为“蓝瑞萨”。决定是否向45nm以下的精密化工艺进军是半导体厂商面临的重大战略之一。
因为美国德州仪器放弃精密化,瑞萨就乱成一团,这更是不可取的。是否继续推进精密化,应该由制造商自主决定。在恳谈会中我向东芝的领导们询问道:“听说美国德州仪器不会进行45nm以下芯片的自主研发,东芝准备怎么办呢?”东芝的回答是:“德州仪器是德州仪器。我们是我们。我们依然会推进精密化的研究。”这才是一个企业应有的正常反应。为了阻止日本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下滑,日本专门成立了相关联盟。每成立一个联盟,半导体制造商就需要向联盟派遣10名左右的技术人员。如果成立10个联盟,算起来就要将100个技术人员派出公司。
这样一来,半导体企业自身会缩水。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联盟的技术研发基本上没有对成员公司的SOC产业发展起到任何作用。就这样,成立的联盟数量越多,日本半导体所占的市场份额就越小。最终日本SOC产业将迎来毁灭性的结局。美国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该联盟以“在1993年之前夺回美国在半导体业界的地位”为目标,按部就班地实施计划。
实际上,美国半导体所占的市场份额确实扩大了,而日本半导体所占的份额下滑。美国成功反超日本。同时日本半导体产业衰败都是由于美国施压使日本无法采取积极的国家政策而造成的。如果分析2005年后瑞萨的销售额和营业盈亏额,可以发现仅有两年出现盈余,分别是2007年度和2010年度。2010年瑞萨创下史上最高的销售额1.1379万亿日元和145亿日元的营业利润,可营业利润率却仅有1.3%。除以上年度外,公司全是赤字。
同样是生产微控制器的企业,生产个人电脑CPU的美国英特尔在瑞萨创下最高销售额和营业利润额的2010年度获得的销售额为436亿美元,营业利润为159亿美元,营业利润率达36.5%。即使在当今个人电脑遭智能手机淘汰,陷入低迷的情况下,2012年度英特尔也创下了销售额533亿美元、营业利润146亿美元、营业利润率27.4%的业绩。英特尔控制着PC架构本身。
PC的世界是以英特尔为中心运行的。这样,英特尔就紧紧地掌握住价格控制权。但是,在汽车行业里,掌握价格控制权的是汽车制造商,具体来说就是丰田。
瑞萨只不过是按照上级生产商提出的规格及价格要求,规规矩矩地进行生产而已。英特尔和瑞萨的收益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取决于有无掌握价格控制权。
2012年2月,尔必达的破产就像激起了连锁反应一样,一直亏损的瑞萨也被逼入了经营破产的死胡同。瑞萨的三大股东日立制作所、三菱电器、NEC的主要股东如临大敌,与东京银行、三菱银行、三菱东京UFJ银行等4家银行联手对瑞萨注资1000亿日元。这才使得瑞萨躲过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危机。美国的投资公司KKR计划收购瑞萨,希望在年内买下过半的瑞萨已发行股票,得到瑞萨的经营权。
为了阻止KKR,官民基金“产业革新机构”和丰田汽车及松下等民间资本决定共同出资收购瑞萨。KKR的如意算盘最终未能得逞。世界的发展模式瞬息万变,而日本却仍沉浸在30年前的成功经历所带来的沾沾自喜中,深信“日本技术水平世界第一”,没有一丝想去改变自己的念头。可以说,日本半导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原因恰恰在于这种无意改变的态度。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发明和市场的新结合”。更简洁地说,“创新就是产品的广泛普及”。这里重要的是产品能够广泛普及,与技术是否具有革新性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技术研发的阶段是不会出现任何创新的。
只有当使用了这项技术的新产品热卖时才能称得上实现了创新。日本人对此出现了错误认识。他们坚定地认为,要先研发出先进的产品才是创新。正因为存在这种思维误区,日本人非常容易陷入创新的困境。三星的理念是“生产能卖掉的东西”,而日本企业仍然坚持“卖掉生产出的东西”这一理念。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日本电视产业崩溃的原因可以总结为,技术人员以自我为中心、对创新的错误认识、全球化扩展的不充分、市场营销能力的不足。然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从数字电视由模块零部件组装而成这一趋势开始。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制造商只要采购了零部件都能生产数字电视。
1990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前十强中,以NEC、东芝、日立为首的日本制造商就占据了其中六强。此时的英特尔还仅名列第五,而三星更是连前十强都未能进入。
无晶圆厂——晶圆代工经营模式当时也才呱呱坠地,尚没有什么立足之地。然而在此后20年,始终坚持在前十强榜上的半导体厂商却仅仅只有英特尔、东芝、德州仪器三家。而如果再往前追溯到1971年,以40年为周期来看的话,坚守在前十强的企业就仅有德州仪器一家。
由此可见,要预测20年后的事情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情。美国苹果公司在2007年和2010年先后推出iPhone和iPad产品,从此,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飞速普及,而这也给英特尔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正如提出“革新困境”概念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所使用的说法,iPhone引发了“颠覆性革新”。
iPhone颠覆的不仅是传统手机,而且也颠覆了个人电脑。iPhone问世后,曾名列手机市场份额第一和第二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开始没落,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以及戴尔也出现了巨额的赤字。英特尔打造的超薄轻量笔记本Ultrabook的销售业绩萎靡不振。
市场调研机构IHS iSuppli最初预测2012年Ultrabook的出货量为2200万台,此后将之下调为1030万台。而且,还将2013年的出货量从原来的6100万台下调至4400万台。
克里斯坦森教授曾在iPhone发售后不慎失言道:“iPhone也不过是一款徒有其表的手机,不可能一炮打响。”
可以看出,即使克里斯坦森教授是革新困境理论的权威,他也低估了iPhone所内含的颠覆性技术。在PC机备受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冲击的形势下,再加上低耗电的ARM处理器的冲击,英特尔公司甚至在PC处理器市场也难以再继续维持其独霸天下的局面了英特尔虽多次尝试通过Atom处理器进军手机及智能机市场,但均以失败告终。
2012年世界智能机处理器出货总量达7.1亿个。从企业品牌所占的市场份额看,第一位是美国高通(Qualcomm,36%)、第二位是美国苹果(20%)、第三位是韩国三星电子(11%)。
英特尔仅占0.2%。智能机、手机处理器的基本设计(体系结构)95%都采用ARM处理器。ARM技术体系不仅限于智能手机,还广泛应用于通信设备、游戏机等移动设备,甚至还包括路由器、汽车半导体等。
2011年,ARM处理器销售量高达79亿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特尔作为PC处理器的销量冠军,其销售量仅有3.3亿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厂商大举来袭,英特尔迅速失去了市场份额。
1984年英特尔的市场占有率甚至一度下降到了1.3%。在这种情况下,摩尔试图将DRAM作为英特尔发展的技术核心驱动力,开始寻求对DRAM业务的强力发展。但此时,公司内部也开始将重心逐渐转移到处理器。
DRAM部门坚持抗争了1年,但最终,公司还是停止了对1MB DRAM的研发。互联网及手机开始普及。面对这种新形势,贝瑞特开始大规模收购其他公司,试图使英特尔由PC处理器生产企业转型为手机及互联网企业。然而,被英特尔收购的公司的领导们根本不能融入英特尔的企业文化之中,很快就提出辞职。祸不单行的是,英特尔公司内部也是一片混乱。
苹果(可能就是已经去世的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向英特尔表达了合作的意愿,考虑将第一代iPhone处理器的生产委托给英特尔。据说,当时苹果提出会支付给英特尔一定的金额,但是除此之外绝不会多给一分钱(这种说话方式充满了乔布斯的风格)。估计当时乔布斯开出的价格为每枚处理器10美元左右,并表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于是英特尔进行了一系列的测算:根据这个开价,想盈利要确保多少的生产量,而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取决于iPhone能获得多少销售量。只是英特尔当时千算万算都不会算到,将来智能手机的出货量竟会超过个人电脑。因此,英特尔认为,制造这种单价10美元左右的处理器根本没有赚头(顺便提一下,英特尔生产的PC处理器每枚价格为5000~20000日元)。基于这种推测,欧德宁最后回绝了苹果提出的委托交易。英特尔回绝了苹果的交易邀请,于是iPhone处理器的生产供应商最终变成了韩国的三星电子。
在iPhone效应的积极影响下,仅用了3年时间,三星在晶圆代工行业的排名就由第10位飞跃到了第3位。后来,三星生产的智能手机Galaxy的出货量超越iPhone,荣登世界第一的宝座,同时该手机也成为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在Galaxy的研发及制造过程中,三星运用了很多生产iPhone处理器时获得的技术窍门和要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当时英特尔承接了苹果的委托,历史可能就会由此改变。也许英特尔会在如今日思夜想的智能机处理器领域确立稳固的地位,不用挣扎在“英特尔历史上最大难题”的泥潭中,而欧德宁也会因为成功发展新业务而被歌功颂德,也许如今他还在CEO的宝座上指点江山。
相反,现在吃苦头的有可能就是三星了。没有了iPhone效应,三星可能无法在晶圆代工业务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现在公司的摇钱树——Galaxy手机也有可能不会问世。然而2013年,台积电成功从三星手里夺走了iPhone处理器的生产业务。还有消息称,2014年以后,英特尔会加入iPhone的代工业务。
相比于1998年,2012年英特尔的销售额增长了2.2倍,三星增长了6.5倍,而台积电竟然高达11.2倍!而且从雷曼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即智能手机真正开始普及的年份)开始,台积电的营收增长率在3家企业当中也是位居第一。在这个时候,最先成功掌握铜布线工艺的,就是富士通和NEC等日本半导体制造商。
台积电的铜布线成品率却一直裹足不前,受此影响,几家手机半导体设计公司(无晶圆厂)接连倒闭。一直以来由台积电承接的无晶圆厂的项目也转到了富士通手中。由于事业进展不顺,如今,富士通拟将位于日本三重县的工厂出售给台积电。此外,富士通旗下的设计部门也将与松下合并。业。
随后,凭借最先进的精密加工技术,英特尔率先研发出3-D三维晶体管技术,并从台积电手中抢下一桩生意。这样的情节,简直就是富士通的翻拍版。估计有这种感觉的应该不止我一人吧。
该报道称,2006~2007年时,中国台湾制造的DRAM和液晶面板很畅销,三星对此深感威胁,于是派出多名企业高管亲临中国台湾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并制定了逐步摧毁中国台湾IT产业的“灭亡中国台湾计划”。
首先就是给中国台湾的DRAM产业施压。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三星依然坚决进行设备投资,受此影响,中国台湾的力晶科技、茂德科技等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最终在2012年退市。
其次就是打压中国台湾生产的液晶面板。具体表现就是三星大幅缩减从中国台湾采购的电视面板数量。此外,2010年,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几家液晶面板生产巨头被欧盟以“卡塔尔(垄断性企业联合)”为由开罚单,而三星却得以幸免,原因就是三星曾向欧盟当局提供相关信息告密。
第三点就是进攻中国台湾智能手机产业。
第四点是阻止夏普和鸿海联姻。五点就是进攻中国台湾的晶圆代工业。
不仅是半导体,纵观日本二战后的产业历史,无论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纤维产业及钢铁产业,还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汽车产业,可以发现,日本获得成功的产业都有以下三个特征。
1、竞争力扎根于制造工序的产业:通过在产品的生产现场实行TQC(全面质量管理)和改善法,来提高生产效率,并形成竞争力,这样的产业是日本的强项。相反,需要在研究、市场营销和销售方面提高竞争力的产业则是日本的弱点。
2、需要高度集成技术的产业:需要将多个组件技术组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集成的产业也是日本的拿手项目。相反,模块化的产业以及单凭一项拔尖技术就能形成竞争力的产业则是日本的劣势。
3、要求延续性技术的产业:日本擅长要求技术持续进步的产业,而不擅长对技术延续性没有要求、技术变化频繁的产业。
综上所述,日本在半导体存储器领域取得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相比于设计,日本在半导体的制造工艺方面更能形成竞争优势;其次,半导体对集成技术要求很高;再次,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需要以比例缩小规则及摩尔法则为理论基础,依次推进精密化和高集成化。这些都是日本人擅长的领域,因此能够获得成功。
相反,在SOC领域,相比制造工艺,产品的销售计划,以及为确立计划所进行的市场营销,还有系统设计能力,这些因素更容易成为优势竞争力的源泉。
这些因素中很多都是日本人不擅长的,所以日本的SOC产业未成气候。精密加工业务曾经是日本的看家本领,但是最终日本还是自宝座跌落。
在曝光设备方面,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取代了尼康和佳能,一举占据了将近8成的市场份额;干法刻蚀设备方面,美国泛林研发超越东京电子(TEL)坐上第一的宝座;晶圆检测设备方面,美国科磊独占半边天;PCVD和溅射等成膜设备方面,美国AMAT紧握霸权。
曝光设备的ASML,干法刻蚀设备的泛林研发,晶圆检测设备的科磊,成膜设备的AMAT,这些企业在战略方面都有一条共通的主线:即标准化、平台化及模块化。换言之,上述欧美设备制造商利用设备的综合系统化能力和架构能力来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并最终获得了最大的市场占有率。
大日本屏幕制造的清洗、干燥设备,东京电子的匀胶显影机,荏原制作所的CMP设备,这些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使用液体材料。比如,清洗、干燥设备需要洗涤用的药水,匀胶显影机需要感光性的抗蚀剂,CMP则需要浆体研磨剂。
曝光设备从引进到投入生产,主要经过机械元件组装→设备安装→设备性能测试(企业标准)→设备性能测试(顾客意见)这些程序。从设备引进到投入生产,间隔最短的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只用9天。
在这期间,企业不进行任何性能测试,硬件一旦组装完成马上就开工生产(对于完全省略掉性能测评环节这一点,我认为有点操之过急了)。
其次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在硬件组装完成以后,用1~2天进行企业标准的性能测试,在11~14天后将设备投入生产。相比从引进到开工只花费9天的中国大陆企业,日本企业所花费的时间加起来已逼近40天。
无论ASML如何重申“我们的设备不需要进行任何追加的性能测试”,长期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研发曝光设备的日本制造商也只当耳旁风,一遍遍重复着多余的性能测试。
奥戴德·石家安的学者写的一本书,书名是《模仿的力量》。我看过后就确信,这本书其实是针对三星电子的一个案例研究报告。但书中几乎没有出现三星一词,这倒反而让人觉得作者是在有意掩饰。
石家安指出:“模仿是稀缺且复杂的战略能力”“模仿是进行创新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作者开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但是随着深入阅读,我发现石家安的论点非常新颖且具有说服力,在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心目中对于模仿的概念和认识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贾德·梅森·戴蒙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该书日译版已由草思社文库出版)中就提出:“没有模仿,人类根本不可能进化”。而且,这个结论有实例支撑。
举其中一例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系统都是由苏美尔楔形文字或玛雅文字派生、改良而来的,或者说是受两者影响而设计发明出来的。
此外,水车和磁针等重要技术的发明在世界上也就那么一到两次,接下来全是模仿、模仿、再模仿。也就是说,社会通过模仿来获得其他社会所拥有的更优异更先进的东西。没有模仿,这个社会根本不会存在。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也可以发现模仿遍布于人生的各个阶段。其实在学校的学习基本上都是在模仿。通过模仿学会字词的读写,通过模仿学会计算加减乘除。连思考方法都是通过模仿掌握的。可以说中考和高考,测试的也许是学生的模仿能力。拿企业的案例来分析,IBM曾在大型计算机业务上落后于雷明顿兰德,但是IBM奋起直追,通过模仿,4年内就夺得市场。此外,IBM效仿AppleⅡ研发了IBM PC,被经营学家彼得·德鲁克称为“拥有世界第一业绩的创造性模仿者”。
美国雅达利(ATARI)于1975年推出家用游戏机乒乓后,有75家公司竞相模仿,日本任天堂也是其中一家。然而随后,任天堂生产的游戏机逐渐发展成为行业的国际标准。
在网页浏览器方面,网景效仿斯普莱设计出的浏览器进一步被微软模仿,最后演变成IE浏览器。微软凭借模仿而来的IE成功垄断了市场。甚至在石家安口中,苹果也是模仿者。比如,苹果麦金塔电脑的技术基本上都不是苹果自主研发的。据说Mac的可视化界面其实是史蒂夫·乔布斯在访问施乐的帕洛阿图研究中心(PARC)时才萌发灵感、有了设计构思的。
此外,iPhone同样模仿了现有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这个技术和新思维相结合。所以有人才会戏言,苹果是东拼西凑的高手。如果模仿能够成功,就能省下相应的产品研发费用。此外,还能降低产品被市场淘汰和企业破产的风险。美国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让人哗然。
该调查研究了从1948年到2001年间诞生的发明创造,发现这些创造的发明人只能获得自己研究成果现有价值的2.2%。也就是说,价值的97.8%基本都进了模仿者的腰包。以DRAM制造商的身份启程挺进市场的英特尔在第1任CEO诺伊斯当权时,就凭借4KB DRAM抢占了超过80%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美国国内的其他公司纷纷效仿、蜂拥而至,英特尔的市场占有率急转直下。于是英特尔致力于研制16KB DRAM(三电源供电)和64KB DRAM(三电源供电),然而身后有跟风模仿的竞争对手穷追不舍,想要垄断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个技术最终被竞争对手,特别是十多家前来叫板的日本企业模仿、攻破,这导致1984年英特尔的市场占有率跌到10%左右。256KB DRAM的市场占有率更是不到1%,无奈之下英特尔决定停止研发1MB DRAM,并在1985年从DRAM产业中狼狈退出。
英特尔的退出,使日本产的DRAM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功占领世界市场80%的份额。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星电子成了市场的领头羊。通过实行战略性模仿策略,后起之秀三星不仅在DRAM产业登峰造极,在NAND闪存、液晶电视和智能机领域也是势如破竹,成功问鼎世界第一的宝座。
石家安指出,通过模仿获得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企业都有法宝让自己凌驾于原版之上。日本自古以来就是擅长“创造性模仿”的高手。就像石家安为《模仿的力量》日文版所作的前言中提到的那样,日本从很早以前就通过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等方式广泛效仿周边国家的思想、文化与政治体制,并且日本并不局限于单纯模仿,还加以改造,努力使模仿来的知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广泛探究了欧美列强在各领域的思想创意和先进模式,积极加以模仿、引进,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外来思想、技术与本国实际情况的完美嫁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以美国为范本,在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产业推行创造性的模仿策略,最终被誉为“世界第一”。
此时,日本以体形小巧、价格低廉、质量优越的产品抢占了市场,最后甚至超越了曾经的范本——美国。然而,日本在到达世界之巅以后就开始减速,到2012年日本的电器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终于全线崩溃。导致崩溃的原因正如石家安所指出的:日本人认为“跟随和模仿的时代已告终,从今往后是日本人独立创造的时代”,这等于否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竞争力的源泉——模仿能力。日本半导体及电器产业应该重新唤醒曾经毅然舍去的模仿能力(本来日本应该对此非常擅长),这才是获得重生的捷径。